□姜媚
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,没有完成时,其重点在于化风成俗。
要实现化风成俗,需要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精神滋养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积淀,正是化风成俗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和精神沃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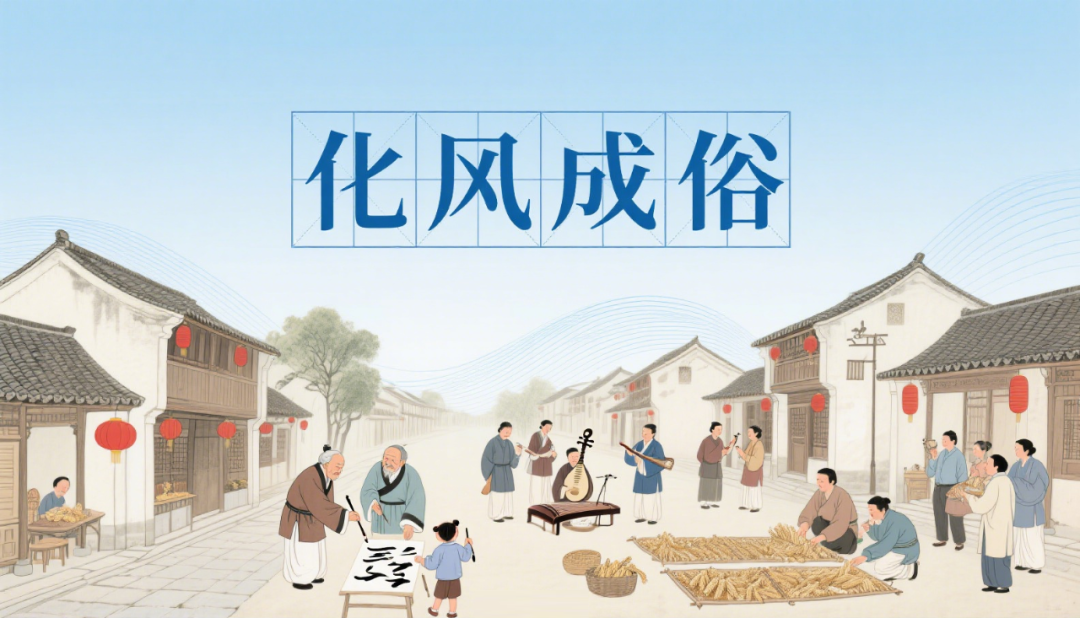
▲图片为豆包AI生成。
“风”与“俗”,互为表里。
典籍中,“风”源于《诗经》国风,初指各地民歌谣谚,后引申为特定地域民众普遍的生活习惯与精神气质。
“俗”者,《说文解字》释为“习也”,是长久形成、代代相传的行为模式。
风俗,也可以说是区别于正式制度文化的、人们心照不宣的一种“文化秩序”。
中国古人,很早就认识到“风俗”的重要性。
荀子明确主张“移风易俗,天下皆宁”。《汉书》说“风行俗成,万世之基也”。东汉学者应劭,则将“辨风正俗”视为“为政之要”“最其上”的位置。
历史上,很多主政者通过“观风俗”察“得失”。
周代设置采诗官,深入民间采集歌谣,将其编纂成诗呈现给天子,以此体察民意、调整政令。
西汉时期,汉平帝为了解地方情形,特遣王恽等八人“分行天下,览观风俗”。
风有薄厚,俗有淳浇。风俗会随着历史延续而传承,或是变化。这种传承和变化差之毫厘,则失之千里。
比如,汉代循吏文翁治蜀,感于“蜀地辟陋有蛮夷风”,于是力倡教化,兴办官学,一改蜀地旧俗,终使“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”。
又比如,唐代天宝以后,“风俗奢靡,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,而居重位、秉大权者,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,曾无愧耻。公私相效,渐以成俗”,以致积重难返,陷入风雨飘摇。

▲向“舌尖上的浪费”说不。(邓尧/绘)
风俗好坏关乎社会盛衰,从古到今,“化风成俗”“移风易俗”成为贯穿始终的社会治理命题。
一种风气,要成为被广泛认可的文化自觉,需要经历“行为—习惯—风俗”的积淀。这也意味着,化风成俗贵在教化引导、重在落地生根、难在持久深入。
纵览历史,我们不妨从古人智慧中汲取养分。
以规成习,刚性约束。在中国古代,通过选官、考核、监察等制度,将“风俗”相关内容作为官员的重要评价指标。
古代选官,常把“德行”作为入仕门槛。汉代举“孝廉”,要求被举荐者必须“善事父母、清正廉洁”。后来,北宋科举设“经明行修科”考察人选德行,明清科举要求品行无缺,都是将“品行端正”作为选拔官员的条件,这些品质本身就是对社会风俗的示范。
在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中,也把“品行端正、能为风俗表率”作为重要内容。比如,唐代用“四善二十七最”对官员进行考核,其中德行要求的“四善”(指德义有闻、清慎明著、公平可称、恪勤匪懈),列在官员具体才能标准的“二十七最”之前。

▲图片为豆包AI生成。
古代还通过监察体系,纠察官员“伤风败俗”等行为。比如,明太祖时期规定,官员不得“狎妓饮酒”,若违反,不仅受罚,还会被作为反面教材公告。
以上率下,示范引领。《左传》云“风成于上,俗化于下”,强调上层的行为示范对民间习俗的决定性影响。北齐刘昼在《刘子·风俗》中,作了进一步阐述:“上之化下,亦为之风焉;民习而行,亦为之俗焉。”
社会风俗由人的行为反映出来,多源于“上行下效”。以上率下、榜样示范以期弘扬风尚的做法,从古到今都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。
春秋时期,晋国曾盛行奢侈之风,晋文公以身作则,“衣不重帛,食不兼肉”,即不穿双层丝绸、不吃两样肉食。不久国人效仿,“皆大布之衣,脱粟之饭”,风俗为之一变。
东汉初年,刘秀为扭转乱世风气,树立卓茂、祭遵这两位官员为楷模,二人的事迹分别衍生出“束身自修”“克己奉公”等成语,成为东汉官场廉洁符号。
当下,抓“关键少数”成为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着眼点,这与古人的智慧是相通的。

▲务实善为写好“为民答卷”。(钱静洁/绘)
以文化人,自省其身。明代首辅李东阳认为“论吏治,则先风俗”,即首先要考虑风俗对官员的影响。通过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,推动官员群体成为化风成俗的表率,是多个朝代治理的重要逻辑。
《礼记》说:“君子欲化民成俗,其必由学乎。”一个“学”字,强调教育、教化,本质上是以文化人。
中国几千年历史中,儒家主张“为政以德”,认为官员之“德”是治理的根基,将官员的“德”转化为一种文化影响力。
同时,代代相传的“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等理念,引导古代官员群体“修”个人品德,强化自身约束。
清代张伯行在福建任巡抚时,撰写《禁止馈送檄》,自己带头“不收受礼品、不赴私宴”,福建官场“馈送之风”遂止。
明代薛瑄任广东道监察御史期间,出监湖广银场,在众人眼中,这是“肥差”。薛瑄举古诗“此乡多宝玉,慎莫厌清贫”谢过众官员祝贺。到任后,他查禁贪污,匡正风气,并在寓所照壁上题诗明志:“有雪松还劲,无鱼水自清。沅州银似海,岂敢忘清贫。”赢得当地百姓一致称赞。
从规制条文升华为文化基因,从外部约束到内化于心,照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“正人心、厚风俗”的理念。
从历史中走来,读懂“化风成俗”的长期主义和历史周期率的破解密码,对于当下的作风建设不乏启迪意义。

